-
画院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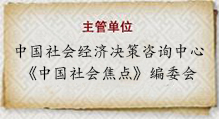 《人民书画院》隶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中国社会焦点》编委会事业非法人组织,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专业书画院。 《人民书画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为服务人民,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中国传统... [详细]
《人民书画院》隶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中国社会焦点》编委会事业非法人组织,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专业书画院。 《人民书画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为服务人民,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中国传统... [详细]
-
联系我们
-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环中路8号院钓鱼台山庄36号楼附楼
网址: www.rmshy.org 电话: 13910449081 010-53672178 传真: 010—53672178 邮箱: zgrmshy@126.com
-
贾平凹谈《极花》:小说生长如同匠人在用泥巴捏神像时间:2016-05-04 17:24 点击率:

贾平凹澎湃新闻记者赵振江图
路遥在世的时候评点过贾平凹的名字,说“平字形如阳具,凹字形如阴器,是阴阳的交合体。”
贾平凹回应对朋友的戏谑:“可名字里边有阴阳该能相济,为何常年忙着生病,是国内著名的病人?”事实上,和同样患乙肝但英年早逝的路遥不同,64岁的贾平凹创作力旺盛,继2011年出版67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之后,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2013年《带灯》、2014年《老生》,今年又让《极花》登场。
“你不要再写了,写得太多了,人家还没看完上一部你就快写完下一部了。”4月14日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贾平凹说有人这样开玩笑劝他。但在他看来“写作是我生存的一个方式,再一个,我自己心里有一些事情,写过了才能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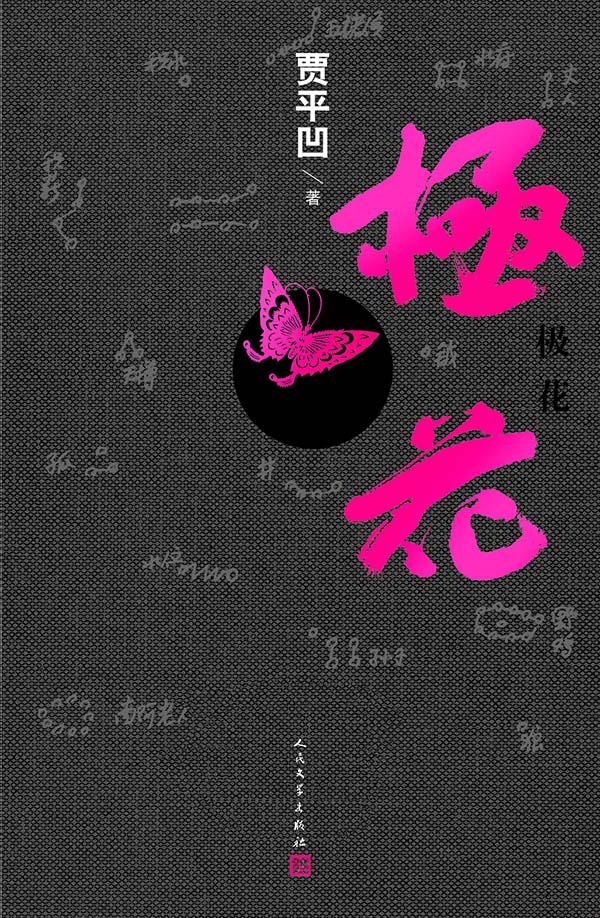
《极花》书封
“那个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
这些不安宁很多来自于他和老乡的交流与他对农村的观察。尽管19岁就离开陕西省棣花镇,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极花》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十年前准备小说《高兴》时与拾破烂的老乡的交流。老乡有一次向他诉苦,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废品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找了整整三年,好不容易女儿被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贾平凹在后记里写到当年的心态。
这个真实的故事,贾平凹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他的心里,每每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
面对这个题材,“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了数百页的文字后,写不下去了。”贾平凹说,直到前两年跑过农村好多个地方,多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才获得他想有的写作感觉。
“高速公路沿线,有一些村庄,这次我跑回去,只有在那个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其他完全没有人。从门缝里看进去,黄草半人深。跑到我们乡镇南山和北山,就是南区和北区,走访了比较偏远的村寨子,在我前几年去的时候,村寨人少,村和村合并。去年我去了以后,乡和乡要合并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贾平凹在2015年的夏天开始动笔,“《极花》中的极花,也是冬虫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虫子,而且小虫子冬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长草开花,要想草长得旺花开得艳,夏天正是好日子。”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贾平凹在后记中介绍,原定的《极花》里,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日子垒起来,成了兔子(胡蝶的儿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村子里的妇女),成了又一个訾米姐(另一个被卖到村子里的女人)。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十五万字画上了句号,天劈里啪啦下雨,一直下到傍晚。这是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贾平凹在等着外出的家人,思绪如尘一样乱钻,突然就想起两句古人的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作家贾平凹介绍《极花》创作情况
【对话】
“写作可能解决心神不安的问题,但写作又会害得我心神不安宁”
澎湃新闻:你在后记中为什么会引用苏轼写给姜唐佐的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及石延年的“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贾平凹:这个有偶然性,就是脑子转到那儿了。“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的意思是,不管社会怎么发展,文学还是消亡不了的,社会也还是会一直往前走的。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生命依然在散发着华丽的光彩、生命的快乐,乐意相关,人和人之间只要乐意相关,鸟儿都开始说话,树和树之间不断交叉、不断开花,美好的东西继续。并不都是带给人绝望的东西,我写这个东西也不是让大家来绝望的。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感觉,并不是明指的。另一个我觉得这四句诗有意思,第一句写得很豪言壮语,第二句写得那么温情优美。
澎湃新闻:你提到水墨画对你创作小说的影响,除了在理论上写意的方式,具体的技术上对你有何影响?
贾平凹:从结构写作角度来讲,原来是线性结构,慢慢来。西洋画更多的是油画里的色块,油画里面涂抹出来的那种色块,里面没有线条。中国画里面的模糊画法,也是没有线条的,它是大量的晕染,你看那个先锋小说,写到一个事情、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大量地渲染,一切都有色彩,交融起来给你一种快感、痛快淋漓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色块一个色块的,不讲究时间的顺序、时空的顺序。
中国的小说原来也是串糖葫芦那样的,一个色块一个色块的、一疙瘩一疙瘩的,大致差不多。但是西方的色块是放大的,特别大、特别夸张荒诞,显得很极致。
这两三句说不清楚,是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说出来不一定准确到位,但就是这么个意思。
昨天我也谈到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关系,现在强调一定要有集体意识,其实就是大家共同思考的,你说出了大家共同想到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写出大家公同的感受、通感,不要写纯粹是你个人的东西。
举个例子:比如一车人去旅游,司机在前面开,到了九十点,你说‘司机把车停一下,我们去吃饭吧’,我估计满车的人都不同意,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不饿。等到12点,你说停下来去吃饭吧,全车人都会响应你。在表达集体意识的时候,你把个人的意识写得越独特越精彩越好。
在写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这个人的命运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某一点交叉,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时代的命运在某一点契合交集了,把这一点写出来,那么个人的故事也就是社会的、时代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这就像你在家门口种了一朵花,但是它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了,因为你闻到这朵花的芬香的时候,每一个路过的人也都闻到了芬香。
澎湃新闻:在你的作品中有一个类似于圆形时间的概念,比如《极花》的结尾同时也是一个开始,书中的胡蝶离开又返回去,你怎么处理作品中的时间概念?
贾平凹:任何事物的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都是一回事,比如用水熬鸡汤,把鸡捞出来,鸡汤也是水,但鸡汤的水和开始的水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极花》中的人物,黑亮是不是代表了乡村和城市的和解趋向?
贾平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呀,这个媳妇儿,他(黑亮)一定是要保护她的。但是这个媳妇儿又不和他同床,他也不能接受这个,后来在暴力下完成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是特别复杂的,人性中有慈善的也有凶残的东西,就看因时因事展现出来。
为什么不把黑亮设计成一个残疾人,或者是个黑社会或者凶暴、野蛮的人?也是因为对蝴蝶有同情心,不想让她遭罪,那么好一个姑娘,不想让她受罪。再一个,如果黑亮是一个凶残的人,蝴蝶就算是死也不愿给他生孩子,最后也不会再回去。
澎湃新闻:胡蝶一方面作为书中的一个人物,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全知全能、灵魂出窍的叙事角色?
贾平凹:从叙事角度来讲,如果只作为一个人物就不能更多地表现环境的东西。只能灵魂出窍,否则她不可能把自己被强暴的东西写出来。在窑里的情况,也写不出来呀。
她一开始也不想活,想死也死不了,折磨了将近一年半,用绳子拴着,后来生了孩子、做了母亲以后,心疼孩子,毫无办法,只好委屈地在那儿生活。一旦生活了以后,她也得在那儿洗脸、吃饭,一切正常进行。
现实的逃生情况是这样的:县上来了一个人,有手机,她借手机拨电话,跑到后面的山上,还拨通了电话,但刚拨通就被要回去了。后来有人就根据这个电话找到了她。
胡蝶一直想跑,每天都想跑,却不知道往哪儿跑。这就好比陕北有一个马兰农场,上世纪八十年代关押了几十个犯人,一个狱警看着这些犯人出去劳动,这些犯人经常跑。但狱警也不怕他们跑,因为跑出去方圆几百里就没人了呀。这个环境就是书中胡蝶所在的地方——能往哪儿跑,都不知道啥地方,根本没有路,只要有人发现你,就把你抓回来。
澎湃新闻:书中有一个“老老爷”的设置,在你以往的作品中都有类似的角色?
贾平凹:他代表当时中国农村最老的象征的东西——过去中国农村几千年维持下来的机制:宗教、寺庙族长、族规等,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只剩下政权、法律、金钱三条线了。原来各种线多得很,过去乡村有宗祠家庭伦理等,儒释道各种神仙,牛有牛王,山有山神,土地、灶王、山神,所有神管着,族有族规,有寺院学堂,一切精神都控制着乡村的这一切,很有秩序。老爷爷代表当时农村最高的象征,他也想维持但是也无可奈何了。
澎湃新闻:你在《废都》的后记中提到“鬼魅狰狞,上帝无言”,你的作品中有一些神秘感,从源头上是否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有关?
贾平凹:我的老家是在秦岭的南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交汇的地方,秦和楚,秦强大了就把界线划到楚,楚强大了就把界线划到汉梁边上。那里又有秦代表的中原文化、雄厚的东西,又有楚文化,所以楚文化里有很多巫鬼的东西。在我的那个山区小村,巫文化影响很大。
澎湃新闻:书中写了乡村的困境和你面临的困境,到现在的位置和阶段你面临什么困境?有什么想做还没有达成的事情?
贾平凹:那多啦。中国的社会极其复杂、诡异,啥东西都可能发生,这个社会中常常容易自己找不着自己的位置,搞不清自己的角色,这就带来惊恐紧张烦闷。实际上,我经常讲的,现在追求身安心安。身安静、心安静,是最大的奢求。中国人大部分是身心不安的。从阅读角度上,阅读是解决心神安宁的一个出口也可能是一个阀门;从写作角度上来讲,写作可能是解决心神安宁的办法,但是在写作中又会把我害得心神不安宁。当然世界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东西。
澎湃新闻:你现在身兼数职,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
贾平凹:影响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有很多活动会议要参加,就这两项就让你身心不得安宁。现在有很多文学会议或者讲课,公对公的活动我肯定不去,但是朋友叫没办法还得去。比如新书发布会,安排很多采访,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就没停,而且大部分话都是重复的话。
澎湃新闻:对创作环境有什么要求?
贾平凹:我喜欢在我的那个写作环境中,在一个并不明亮的房子里,收藏品摆得很满、窗帘也不拉开,空气很污浊。我习惯了,几十年都是那样。我不愿意呆在很光亮的地方,光亮以后感觉到处都在漏气儿,神思老不安定。创作需要全神贯注,一以贯之,在那种环境,摆上那些收藏的东西,它们都在看着你,有意思。嗯,我也习惯了自己的那个环境,哪怕个是狗窝,狗习惯了也会对自己的窝产生感情。
澎湃新闻:来来往往接受了一波又一波的采访,你能不能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这个时代在他们身上的印迹?
贾平凹:我觉得不光接触记者,当然采访过程中接触的都是文化精英,包括我在陕西接触的一些中学生,就让我大吃一惊,觉得人家的思维活跃与敏感性和我当年大不相同。对年轻人很害怕,都成精了。
采访我的记者从我的眼光看也都是年轻得要命的,我经常也在感慨,我在人家这个年龄中,哪儿都不敢去,不敢接触生人,知识面也没有人家广。现在中国世界大同了,接触的东西也多了,思维不一样了,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