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院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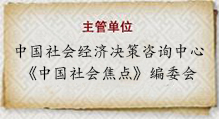 《人民书画院》隶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中国社会焦点》编委会事业非法人组织,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专业书画院。 《人民书画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为服务人民,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中国传统... [详细]
《人民书画院》隶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中国社会焦点》编委会事业非法人组织,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专业书画院。 《人民书画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为服务人民,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中国传统... [详细]
-
联系我们
-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环中路8号院钓鱼台山庄36号楼附楼
网址: www.rmshy.org 电话: 13910449081 010-53672178 传真: 010—53672178 邮箱: zgrmshy@126.com
-
林少华出散文集《异乡人》:不想做村上春树背后的男人时间:2016-04-14 10:46 点击率:
在中国,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与译者林少华的名字紧密相连。从1989年《挪威的森林》开始,林少华与村上春树的作品结下了长达20多年的缘分,是中国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最多也是最著名的译者,由此被誉为“最懂村上春树”的翻译家。上周末,林少华来到上海书城全国新书发布厅第4期现场,但这一次,他不满足于仅仅做“村上春树背后的男人”,而是带来了散文集《异乡人》。
不喜欢名字总是小两号
“如果我的名字总是跟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后面,连字号都要比他小一两号,作为一个男人,不喜欢这种受制于人的感觉。”
作为依靠翻译村上春树作品出名的翻译家,林少华并没有陶醉在村上的世界里,他不满足于仅仅做“村上春树背后的男人”,所以,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毫无村上痕迹、全然代表林少华个人特色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
“咱们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我一个教书匠,‘立功、立德’可能谈不上,‘立言’ 还是可以的,但翻译那玩意不能算立言。我要写一本只署我一个人名字的书。”
从书名《异乡人》来看,仍可以看出林少华和村上春树的确是“一家的”。村上曾说过,“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而在林少华笔下,不管是孩提时代生活的东北山村,还是成年后长期任教供职的广州、青岛,无不有种“异乡”的意味。其次,如同村上春树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刺和揶揄,在林少华笔下,也能看到身为大学教授的他,对于当下物质社会高速发展的忧虑。
翻译就是异乡人的工作
林少华有4种身份,用他自己的定义是:教书匠、翻译匠、不怎么样的学者和半拉子作家,“其中,不用说,翻译匠的知名度最高,影响也最大”。
有意思的是,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林少华,竟把翻译这一工作同异乡人联系了起来。“翻译就是异乡人的工作,加缪也好,村上也好,对于汉语世界,对于中国朋友,都可以说是异乡人,而译者的任务,就是如何安排他们入乡随俗,这在汉语方法上,叫做归化。如果让汉语委曲求全,让汉语尽量向外语靠拢,在翻译上就叫做异化,事实上绝对异化是不可能的,无非是程度和倾向性有所不同罢了。或者不如说,翻译总是在归化和异化之间,保持微妙的张力,总是在两者之间找出融点。”
找到恰到好处的地方,让人欲罢不能,这就是好的文学翻译。“只是,翻译哪怕处理得再恰到好处,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作,异乡人终究是异乡人,再怎么入乡随俗,也不可能脱胎换骨,变成本地人或本乡人。”
没有百分百的村上春树
经常有人问林少华,你翻译的村上,是不是百分百的村上春树?他的回答是:不可能。“其实,不仅读者会追求这样的百分之百,译者也这样追求,甚至有人自作多情,以为自己翻译的村上是百分之百。”
林少华透露:“实不相瞒,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这么自信和猖狂的,但后来有了新的认识后就再也不敢了。我回过头来发现,所谓百分百的村上春树是不存在的,不要说《挪威的森林》等这类纯文学长篇小说,就是I love you这样的短句,翻译起来也是一人一个样。比如刘心武的答案是,研究红学的人会说,“这个妹子我见过的”,足够了。而王家卫说,应该这样翻译,“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坐摩托车了,也很久没有这么近地接近一个人了,虽然我知道这条路很短,我马上可以下车,但是这一分钟,我还是觉得好暖好暖”。
林少华引述了林语堂关于翻译的比喻,即翻译好比女人穿丝袜,“译者给这女人穿上红袜子、黄袜子,袜子的颜色与厚薄就是译者的风格。以我翻译的村上来说,主观上认为我翻译的是百分百的村上,但客观上不是,充其量只是百分之九十,百分百的村上,找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因为任何翻译都是基于自己理解基础上的艺术活动,每个人的感悟和把握不同,翻译只是向译作无限接近的路上,没有终点”。
关注异乡人和文化乡愁
《异乡人》不是林少华的第一部散文集,此前他出版了《落花之美》、《为了灵魂的自由》、《夜雨灯》等多部著作,《异乡人》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感悟,文字充满智慧与禅意。
林少华说,一说“异乡人”这个词,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加缪的同名小说。“他笔下的异乡人,主要是出于人生荒谬的说法,而我这部散文,更多是出于乡愁或者说家园重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有对现实世界的疏离情绪,我创作的目的在于诉求社会良知,呼唤文化乡愁。”
林少华说自己出生在一个“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的地方,村里只有5户人家。年轻时极力想逃出家乡,但现在看起来,永远也逃不出去,因为传统文化的基因在骨子里流淌。当前乡村的变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更涉及文化根基建设,文化焦虑催生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认识到只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与西方在文化上抗衡,从而找到回归心灵的路。
林少华说:“消失的村庄让我这样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感到深深的文化焦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焦虑,而是整个民族的世纪性情绪。我笔下的异乡人,或许首先让人联想到进城的农民工,但其实主要是写家园的流失和精神漂泊者。在宏观层面上,每个人都是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