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院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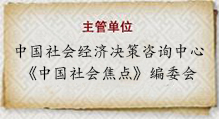 《人民书画院》隶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中国社会焦点》编委会事业非法人组织,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专业书画院。 《人民书画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为服务人民,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中国传统... [详细]
《人民书画院》隶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中国社会焦点》编委会事业非法人组织,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专业书画院。 《人民书画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为服务人民,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中国传统... [详细]
-
联系我们
-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环中路8号院钓鱼台山庄36号楼附楼
网址: www.rmshy.org 电话: 13910449081 010-53672178 传真: 010—53672178 邮箱: zgrmshy@126.com
-
军旅书家李铎访谈录时间:2014-11-06 17:25 点击率:主持人:李铎先生,我们的访谈就从你的“仕龙书屋”开始吧。
李铎:“仕龙书屋”是按李家辈份排下来的,有两句诗“维元开经运,培仕佐生平”。生平就是太平盛世。我父亲是“培”字辈,我是“仕”字辈,我的两个儿子就是“佐”字辈。我是兄弟俩,我是老大,叫李仕龙,弟弟叫李仕虎。所以,我就取了一个“仕龙书屋”。
黄俊俭:能否谈谈你的人生经历。
李铎:我的经历要说起来是很复杂的。首先说说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是一个贫困家庭。土改的时候划为下中农,在土改之前,我们家连中农都到不了,是贫农,在贫农之前还是个佃农,佃农之前,祖辈是在工厂里面做瓷器。我们从祖辈以来都是贫困的。由于这样的家境,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感到很困难。我上学很早,1935年我5岁时就开始上学了,实际上就是读私塾。
记得当时冬天很冷,我的手都冻肿了,脚面也冻伤了,脚后跟都裂了口子,没有袜子穿。后来,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国民党宪党部有一个督学先生,他戴着大礼帽,穿着蓝布褂,手拿文明棍,戴着黑眼镜。其实,这个人的年龄并不很大。到了乡下来,干了四件事:第一是禁毒。第二是禁嫖。第三是禁唱花鼓戏。第四是禁私塾。他这个“禁”按理来讲对社会是有益的事情,但他却是借“禁”的名义敲竹竿。比如,你唱花鼓戏,唱黄色段子就把你抓起来,抓起来以后你得掏钱赎人,这是他捞钱的一种办法。
我们住在乡下,读书很艰难,督学先生来了以后就把私塾关了,成立了一所国民小学,把在私塾里面读书的10多位学生集中起来,在祠堂里面成立了“宜家督清泥湾第一国民小学”,我就开始在这所学校读一年级。
1943年,小学还没读完,日本鬼子打到了我的家乡湖南,把家乡搞得乱七八糟,世界上最坏的军队莫过于日本鬼子,坏事、恶事都干尽了。我们只好逃到山里。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田地荒芜了。
这样没法生活了。我们在山里就不分张家、李家了,都是一家,大家也团结了,也不打架了,有点吃的,互相让着。家里面是真正的家徒四壁,我们的房子都是“干打垒”。所谓“干打垒”,就是在土墙上面盖了一层瓦,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就怕楼上藏着什么东西,他们就用我们南方晒谷子的耙子,把瓦都掀了下来,日本鬼子走了以后,当地的流氓地痞,我们叫“扫地队”,他们先抢着回去,能拿的东西都拿走了。
上山砍柴、扒田、磨米、筛谷,这些活我都干过,但力量不足,我父亲说,你还是学门手艺,学个木匠,或者泥瓦匠也行。后来,邻居段婶把我介绍到醴陵县中和瓷场。中和瓷场的杨老板是江西人,带了七八个徒弟,他收徒弟,但他教不了徒弟,他没有特殊的本事,徒弟在那里学什么呢?就是在瓷器上作画,杨老板自己不会教,他就让我们到别的师傅那里去剽窃,他请一些师傅去画,让我们看人家怎么画,这样去学。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学徒当中我去的最晚,比我早去一天的就叫师兄,他可以指挥你,所以一些苦力活都让我来干,早上5点起来就浸藤子,就是把一捆很大、很长的葛藤绑起来晒干了,绑上石头沉到河里去浸泡。到了下午或者晚上拉上来。扛下去的时候很轻,拉上来的时候很重,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是学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尤其是冬天,手都冻得裂口了。吃饭的时候虽然是同师傅一桌,但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吃,眼睛还得看着师傅手里的碗,等着师傅吃到最后一口,你得赶快把饭碗放下,把他的碗拿过来盛饭。
有一天,我们睡得很晚,我就琢磨起来,我得画点儿什么东西,学点儿什么东西。于是,我就起身,推开门,打开灯,拿一个瓷器在上面画。正当我聚精会神画的时候,突然觉得耳朵跟前有出气的声音,我一回头看,师傅站在我身后,他进来我都不知道。我想,这一顿打是跑不了了,师傅是常打人的,我就站起来把瓷器放下,心一个劲的跳。但他非但没打我,而且还让我继续画,对我说:“你画完早点睡觉。”然后,就走了。
第二天,师傅找我谈话,允许我上案子,就这样,我的地位就提高一步,不用再干力气活了。
我在中和瓷场干了一年多,到了第二年端午节的时候,我就跟师傅讲,我说我离家已经一年多了,想父母了,现在是端午节,能不能让我回去看看父母亲?师傅爽快地答应了。
临走时,师傅还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回家搜罗搜罗,带七八个人来当徒弟。其实,我给他请假的时候就打定主意,不回去干了。我父亲知道了以后说:“不行吧,人家来抓你怎么办?”果然,过了一个星期,师傅派来了两三个人,给了三条路:第一条路,你要是当壮丁,可以不回去。旧社会有一句话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丁”。那个时候,家里有两个兄弟,必定有一个要当兵的,不当就抓,有钱人还好一点,拿着谷子去买一个“假壮丁”,自己的儿子不去。但如果这个人是个“二流子”,你给他谷子,他去当兵,当兵没几天他如果跑了,抓住了以后买壮丁的人是要被枪毙的。
我们家有两兄弟,当兵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父亲不同意。第二条路是上学,师傅断定我们家没有钱,上不起学。第三条路,如果到别人家去当学徒,那我就得赔师傅一年半的饭钱,我给他干了一年半的活,非但没有得到钱,还得赔饭钱,我父亲听了之后气得火冒三丈。一跺脚说:“我们读书。”这个时候,我父亲为什么敢说这个话呢?因为我们家还有几亩地,父亲决定卖地供我上学。
主持人:地卖了,那家里怎么生活?
李铎:家里生活就苦一点。当然,地不是彻底都卖了,还留一些。我继续上学,补习了一个月,准备考初中。其实,我小学没毕业,没有小学文凭,考中学是不允许的,我就托人到山沟里找先生补习了一个月,开了一个证明,去求情。后来,我考上初中了,回家以后感到特别光荣,因为我们当时能读初中的没几个人,能考上初中就像过去科举时期中了状元一样,乡亲们觉得李家出了个有出息的人。后来,我就上了初中,但上学需要办齐14担谷子,一担谷子是一百斤,那时候叫“九六谷”,什么叫“九六谷”?一担是一百斤,用风车使劲摇,这样就把谷子里面稍微瘪一点的谷子吹出去了,真正的谷子就不到一百斤了,剩下有九十六斤左右了,所以就叫“九六谷”。那么,吹出去的谷子里面还是有米的,我弟弟把它们扫扫就收起来,人家还敲敲我们的脑袋说不许拿回去,说这是他们的。到处都是剥削。
就这样凑合着上了初中一年级,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又上不起了,还得借债,借谷子,借高利贷。你借他一担谷子,明年还一担半,50%的利。初中应该是三年毕业,读到二年一期的时候,我再想读书实在是没有钱了,卖地是不能再卖了,把地卖完了以后就没饭吃了,借钱也没法借了,借了没法还。这路又走不通了,还剩下7担半谷子,上一期这些谷子是不够的,没这个先例,交不起谷子就不能上学。可是我不甘心,就跑到学校去,找到训导主任求情。后来,训导主任想了个主意,问我会不会挑水,我说会,我8岁就开始挑水,当时七八岁的孩子在农村干活是很多的,他说你要是能挑水的话就可以抵谷子。我们学校叫湘东中学,靠近庐江边上。这个训导主任住在山腰上,水要从河里挑上来,爬到训导主任家里,路程还是比较远的。我每天给训导主任挑水抵学费。湖南解放以后,大家就不上学了,老师跑了,有些学生也跑了。解放军非常活跃,到处教歌,有两个人教两个,有三个人教三个人,越教越多,最后结成团。1949年8月,学校贴出了一则广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中南军政大学招生,我一看广告就心动了,决定就考这所学校,但中南军政大学条件要求很高,须年满18周岁以上,并且高中毕业的学生,当时我已经19岁了,但没上过高中,而且初中都没有毕业,学历不够。这时候我还不甘心,回家以后就翻字典,一翻就翻到“铎”字,我一看这个字的解释很好,有唤起民众之意;再一个笔画很多,写起来挺好看,而且读音也挺好,不是轻飘飘的,然后我就找招生办,我说我叫李铎。负责招生的人问我:“你是哪一年级?”我说我是初中二年级一期,他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18岁多,他说:“为什么初中还没有毕业你就这么大岁数了?”我就给他讲家里很贫困。这一段讲得好,解放军愿意听,解放军不反对穷人,是穷人的队伍。他说那好吧,明天考试的时候你来,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长。我当时对“特长”两个字还不理解,他说你都会什么吧,我说我会写字,会画画儿。其实,那时候字写得不好,画也不怎么好,只是喜欢,当时就拿起笔写了写,他说好,你明天来,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第二天,我就去考试了,一共考了三门,我觉得很容易。第二天看榜,上面写着好多人的名字,我个子矮,人家都个高,我钻进去,就看榜上两个字的,一看有李铎这个名字,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就解决了我求学难的问题了,有出路了。
说实在话,当时还没有为了保卫祖国这样的觉悟,就是为了找出路,但有一条,找出路我不会找国民党,要选我就选共产党。
主持人:你在参军以后还一直坚持练书法吗?
李铎:对,参军以后,我用一个铁桶,里面放点石灰,一个小扫帚,扫帚比我高。我就提着铁桶,逢桥写桥,逢墙写墙。
主持人:你觉得你的军旅生涯跟书法有什么联系?
李铎:有密切的联系。我长期在部队,部队是打仗的,非常严谨;部队讲究纪律,不能随便乱来;部队讲究命令,说干就干。我现在还留恋部队的生活,我觉得部队的生活对我是一种锻炼,一种性格的锻炼,一种爱好的锻炼,这跟书法有关系。
主持人:也就是形成了你今天的书法风格。
李铎:对,阳刚之气。
主持人:你丰富的经历所建立起来的人生信念是什么?
李铎:我的人生信念是从党校学习开始的,当时学了三本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党史党建》。《社会发展史》对我教育特别深,至今我还记得社会发展史的概念、唯物主义的观念。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化的,确实是有道理的,以前我是信神、信鬼的。
主持人:你能简要概括一下你的书法风格吗?
李铎:我的书法风格是刚劲挺拔、遒劲有力。
主持人:你认为在书法学习中离不开“兴趣、勤奋、悟性、路径”8个字,请你具体阐述一下。
李铎:我在几十年对书法的研习,总结了这八个字。任何人学习书法,都离不开这八个字。首先是要有兴趣,没有兴趣是不行的。有了兴趣以后,还得有勤奋作保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学不好书法的。学书法就是一个坚持,每天都得写。再就是光有勤奋和兴趣也还不够,还得有悟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什么叫悟性?我理解就是拿着一本帖去看,你如果能和帖对上话,那就叫悟性。有了悟性你临帖就快,否则就是抄帖,抄完了以后把帖一放,自己再写,还是那一套,帖是帖,你是你,不能结合。光有悟性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路径,就是方向。路径可以浓缩为四个字:临、立、变、创,即学书的继承与发展的路径。我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讲发展,在发展的前提下讲继承。“临”和“立”是个大的阶段,“变”和“创”也是一个大的阶段。“临”是师法于古代碑帖,求形神俱像;“立”是得到碑帖范本的神韵为己所用,奠定书法的根基;“变”是要多看、多读、多听,广泛吸取众家之长,不囿成规,渐具自家风貌;“创”是要融会贯通,取精用宏,寓学养于点画之中,得风神于笔墨之外,自开一格,卓然成家。我提倡什么路径呢?继承和发展之路,有的人说临古帖不对,要从现代开始,我觉得这个路子不一定对;有的人是只能临帖,不能越雷池一步,那也不行。所以,我主张走继承和发展之路。继承和发展之路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人从学习开始,比方说从7岁开始就进入临帖,临到17岁,10年过去了,不一定就是一个书法家,17岁的书法家有几个?13亿人里面恐怕一个都没有,如果再临10年,27岁,能不能成为书法家?不一定。可能悟性好的,成功早,27岁可以挨上边,如果你再临10年到37岁,成为书法家,这倒有可能。如果学颜体还是跟着颜体走,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还不能作为一个完全的书法家出现。那么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意临,又像又不像,在临帖的时候,眼睛看着帖,手里再写,既有帖上的东西,也有手上的东西,还有从别的地方学来的东西,反映到书法上面,这个时候就不要求你只临一本帖,而是要求你多临,博采众长,就像蜜蜂采蜜一样,是蜜就采,为我所用。慢慢地突出一个“变”字,突出一个“临”,“临”是意临,“变”是变化,变来变去就变出自己的面貌来了,这个时候写出来的字,就不是第一个阶段的像某个人,既不像东,也不像西,学古人又不像古人,学今人又不像今人。我既不像古人,又不像今人,那像谁呢?像自己,这就有了自己的面貌了。
主持人:这就上升为“创”了。
李铎:对,别人就认为你是书法家了。但这只是初步认可,你还要前进,到了中等阶段,就写得比较潇洒了。你再往前走,就是高级阶段。高级阶段写出来的东西可能被人家采纳,被人家临摹,被人家取法,对后人纪念,留存下来,甚至能写出一个传世之作,那就叫超级阶段了。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超级阶段,他也是经历了由兴趣、勤奋、悟性、路径这一过程。
主持人:人生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如事业上的不如意、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待遇上的不公正等。学书过程也存在这个问题,你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李铎:我通常是这样的,遇到了奖励、捧场、吹捧就当成鼓励,奖励也是一种动力,但我决不躺在那张床上。如果碰到了困难、非难,我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激励。林子里的鸟突然飞起来了,里面肯定有点问题,就想办法克服,继续前进,不要灰心丧气,不要颓废不前。所以,毛主席讲革命也有高潮,也有低潮,当我们牺牲同志一大片的时候,我们拍干净身上的泥土爬起来继续前进。
主持人:你当初学书法的时候,是从哪个帖入手的?
李铎:我是从柳体入手的,然后由柳体到颜体,再到“二王”。后来,到北京学郭沫若,学了好一阵,学得很认真,到了乱真的程度。
主持人:你的书法受到哪位书家的影响比较大?
李铎:我受郭沫若的影响比较大,也就是说,我在1959年之前临的是古帖。1959年,我来到北京工作以后,看到满城都是郭沫若的字,这个“满城”可能有点过,但当时能够在报纸上登载书法的就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郭沫若。别人的基本没有。“颐和园”三个字是郭沫若写的,“北海公园”四个字郭沫若写的,“中山公园”四个字也是郭沫若写的,当时凡是公园里的字基本上都是郭沫若写的,“故宫博物院”这五个字是郭沫若写的,故宫博物院里面还有珍宝馆、绘画馆,都是郭沫若写的,写得真好,那是郭沫若一世的精品,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字,那时候我经常到荣宝斋去借他的真迹,他们也支持我。夏天,我光着膀子,毛巾绑着手,因为有汗,放到玻璃板上临摹,还不能弄破原件。
主持人:你现在还每天坚持练习书法吗?
李铎:每天坚持。
主持人: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友情链接: